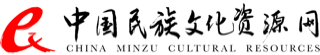杂剧与北方民族
元曲是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唐诗、宋词、明清小说并列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文学类型。元曲一般包括散曲(小令、套数)和杂剧。而人们习惯上说的元曲,主要是指元杂剧。元杂剧的萌芽与成熟期正是我国北方民族女真人、蒙古族统治时期。作为统治民族,他们的民族文化以及艺术喜好、审美情趣等势必要影响到元杂剧的方方面面,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女真人、蒙古族对戏曲的爱好与支持,是元杂剧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。历史上,女真人和蒙古族都是北方民族。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,似乎没有像汉族那么多的封建意识,更没有对民歌、小曲、戏曲的轻视与偏见。女真人的传统民歌,蒙古人的长调、英雄史诗广为流传,深受人民的喜爱。从辽金以来传入中国的音乐,“饶有马上杀伐之音”(徐渭《南词叙录》),结合我国北方歌曲“慷慨悲歌”的传统,形成了新的乐曲体系----北曲。当时的北曲、杂剧与南曲、南戏是相对的,一南一北相互辉映。应该肯定地说,北曲是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、说唱文学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的。而元杂剧里所用的曲调和唱腔主要是继承北曲的传统发展起来的。
元杂剧是以北方方言,尤其是民间口语为基础进行创作的,并以《中原音韵》作为规范。元杂剧对金代“院本”和“诸宫调”的继承是杂剧产生的直接原因。历史上,金代与元代相接,女真人与蒙古人又都是北方民族,他们不论在社会形态、经济类型,还是在语言文化、风俗习惯、审美情趣等方面都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。他们的文化比较容易相互沟通与接纳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元杂剧是金代院本和诸宫调最直接的继承者。元杂剧的那种由一种角色(末或旦)主唱的形式,具有明显的诸宫调痕迹;诸宫调以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的方式,也是由杂剧继承下来了;再有就是用典型的北方口语创作,二者又都是相同的。
在杂剧创作方面,女真人剧作家石君宝、李直夫,蒙古族剧作家杨景贤也是重要的作家。他们的代表作品《鲁大夫秋胡戏妻》、《便宜行事虎头牌》和《西游记》脍炙人口,影响至今。石君宝的《鲁大夫秋胡戏妻》一剧,长演不衰,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李直夫的《便宜行事虎头牌》更是以女真族作家写女真人生活的作品,并且在作品中采用了一些女真人的曲子,在整个元杂剧中独树一帜。杨景贤的《西游记》杂剧,则是吴承恩小说《西游记》之前的最为完整的作品,对于小说《西游记》的产生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这几位少数民族出身的杂剧作家,对于杂剧艺术的发展,对于杂剧题材的拓展,对于杂剧艺术的多样化,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他们及其作品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可见,杂剧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,其萌芽、发展、成熟和繁荣都与北方民族的推崇、支持和积极推动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