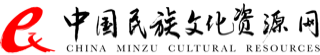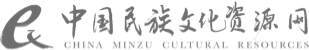抵达桃源秘境的正确方式

山间雾岚轻轻笼罩着乌江

伏羲洞

桃花源景区
对中国文学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,陶渊明那篇传诵千古的《桃花源记》只不过是他的桃花源诗的序言而已。但历史就是这么神奇,那首桃花源诗其实所知者不多,而《桃花源记》却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
我经常想,历史为何会和陶渊明开上这样一个玩笑,原因不外乎两条,一则这符合文学史的特点,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,诗在各种文学体裁里的地位至高无上,而陶渊明本人就是两晋时期最重要的诗人;更重要的原因是,诗里没有为人们提供任何寻找桃花源的线索,而《桃花源记》里却写到“晋太元中,武陵人捕鱼为业,缘溪行”,寥寥十几个字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路线都齐了,这样一来,人们才会反复琢磨吟诵这篇文章,希望自己能成为文字侦探,从中找到通往桃花源的秘径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,这篇《桃花源记》,堪称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一份路书了。
1000年来,桃花源始终没有被找到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反复阅读《桃花源记》的热情。桃花源的魅力大半来自它的隐秘——它惊鸿一瞥地在陶渊明笔下出现后,却又在现实世界里消失了。桃花源,既是一处人人渴望的乌托邦,又是一处无法抵达的秘境。
误入“桃花源”
带着一份对桃花源的好奇,承蒙友人邀请,我在仲春季节来到了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。酉阳的朋友信心满满地说,酉阳就是如假包换的桃花源原型。他们的依据听起来也的确给力:一是此地在东晋时期千真万确就属于武陵郡境内;二是此地水脉众多,古代居民多以打渔为生;三是当地位于武陵山脉深处,古代交通不便,外人不得其门而入,而全国另外几处号称“桃花源”的地方,基本都处于平原地带,“如果桃花源真的在平原上,早就被发现了,这说明真正的桃花源肯定隐藏在山里。”当地的朋友这样说道。
来到酉阳,朋友并未安排直接进入当地全力打造的桃花源景区,而是带领我们来到近几年声名远播的龚滩古镇。我国西南河流众多、水网密集,水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北方,傍水而建的古镇着实不少,这座镇子也不例外,就坐落在乌江岸边。我们下了车,只见一大片古代民居扑面而来,密密麻麻的灰墙黑瓦连绵不绝地覆压着江岸,远望过去,大片的深色色块中还盘绕着一缕缕银色丝线——那便是镇中的巷子。镇子周围少有现代化的痕迹,若不是江边停着几艘硕大的亮银色游艇,我还以为穿越到了古代。同行者中有不少北方作家,对于这种典型的南方景致兴致极浓。很快我们进了镇子,在各处古戏台、古宅院和售卖各种民俗文化产品的店铺里流连,被路旁各种渝式小吃牵引着脚步。
我出门在外一贯的风格是信马由缰,脚步迈向何处,完全由手里面的相机取景框决定,可谓“有组织无纪律”。这次在龚滩也不例外。渐渐地,我和大队人马脱离了。等到同行作家的说笑声、导游字正腔圆的介绍声消失了,面前的景物已经不复刚才的商业气息,变得烟火气十足。各种饭铺、纪念品店铺的招牌看不见了,路旁皆是正宗的民宅。有拖着鼻涕的男童坐在门槛上玩纸片;有皱纹深重的阿婆围坐在街边打着纸麻将;也有晚醒的妇人头顶蓬乱发式,抱着装满衣物的木盆,掩口打着哈欠,沿台阶走向江边。我端着相机,在错综复杂的窄巷间行走。
蓦然,镜头被一大片幽深沉静、明暗交错的蓝色所占据。我抬起头,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一处青石铺就的江边码头,面前二三米外就是闪着细密粼光的宽阔水面。这水面一直延伸到数里外的峡谷,在那里,黛青色的山影和渐渐收窄的江面融合在一起,天地的界限消失了。我正惊叹于水色的变幻和江景的开阔,突然看到从对面江岸的密林中,一道白茫茫的雾气飘过江面,跃上古镇层层叠叠的屋顶,渐渐消散于远处的山巅。这道雾气仿佛魔术师手中的魔法棒,本来肃穆壮阔的画面一经点染,顿时变得灵动起来。太阳一路攀升,光线把江面照得亮如镜面,那道雾气随时可能化为乌有。我感慨着自己的好运气,用相机连拍了一番后,摸出手机打开拍摄功能,屏住气——仿佛粗重些的呼吸,就会吹散这道神赐的水汽——又拍了一通。我把照片发到朋友圈,很快引来众多点赞。
回城的路上,我看着相机里的画面,心想,这大概算是一次迷你型的“误入桃花源”了。
流连桃源秘境
第二天, 我们来到了桃花源景区。据介绍,景区是完全按照《桃花源记》里的布局设计的。进了景区,先被领进了一处暗不见光的溶洞中。这倒也对,《桃花源记》里写得清楚,“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,从口入。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”。我们在溶洞里走了一阵子,眼前的石笋、石花、暗河形态各异,的确值得一看。可在溶洞里越走越深,大家感觉不大对劲,文章里明明写着只需数十步就可通过呢。问导游方知,这个溶洞名为“伏羲洞”,足足长达3公里,是本地新开发出来的景点。我们心想,这个溶洞倒是这次游览的意外之喜,算得上“桃花源中的桃花源”。
这处溶洞不但开发得晚,从地质学上来说,和国内其他知名溶洞相比,也是比较年轻的。年轻有年轻的好处,洞内的石笋比起别处石笋那粗如梁柱的轩昂架势,别有一番纤细玲珑之美。尤其是那些密集在一起的石笋、钟乳石,在各色灯光的照映下灿烂耀眼,远远望去宛如一丛丛布满崖壁的山花。若是溶洞的岁数再大上50万岁,按照钟乳石每年增加十分之一毫米的增长速度,石笋变得粗大了,甚至地面和洞顶相贯通,变成一根石柱,反倒没什么可看了。
等出了溶洞,眼前果然“豁然开朗”,满眼都是青翠疏朗的田园风光,既有大片的油菜花用灿烂的金黄色冲击着人们的视线,也有青灰色的茅屋和曲径通幽的碎石小路,让景致变得柔和起来。而在小径的两侧,处处可见大丛的桃花、杏花。此时,在我所居住的北京,只是有些迎春花在细嫩的枝条上缀上几点零散的黄花,离如此春意盎然的景致还早着呢。在这里盘桓了一阵,我们渐渐看明白,当地所希冀的,是利用原本的地势地貌,再辅以最小程度的修葺,以尽可能天然的景观,向陶渊明笔下靠拢。
和《桃花源记》所写的一样,小路旁的田地里,老人穿古装在田间劳作。他们见游人从小径深处杂沓走来,就拄着锄头,脸上现出着谦和羞涩的笑。老人们挥动锄头的动作虽不乏表演成分,但笑意是真实的。这笑既是出于对现世生活的满足、对远客的善意,亦是出于自己模仿者身份的腼腆。时近晌午,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来给一对老年夫妇送饭,他们擦擦手在田埂边坐了,你一勺我一筷地吃了起来。这无意间的场景,恰恰就是《桃花源记》里的“长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”的真实再现。
心灵理想国
在桃源秘境游览一番,虽养眼舒心,但终归只是农田村舍,还谈不上令人惊叹叫绝。正如《桃花源记》中没有描绘桃花源中的景致多么美妙,却将笔墨留给那里的人心和善、民风淳朴一样,说到底,桃花源的风景如何,在陶渊明眼里并不重要。
体悟这篇《桃花源记》,其实还必须和陶渊明的另一个故事联系起来,那就是他“不为五斗米而折腰”。面对官场里的繁文缛节,面对骄横不可一世的上司,陶渊明毅然挂冠而去,归隐田园。后人惊讶于他的勇气和骨气,但对于陶渊明来说,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选择。时时浮现于他脑海里的桃花源,就是他渴望的理想国,一方时刻呵护着他心灵的乐土。精明者或许会说陶渊明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,官位、俸禄、前程,人们敬畏的眼光、奉承的话语,这些原本唾手可得的一切,都在他走出官衙的那一刻烟消云散了。但在陶渊明看来,自己失去的只是桎梏,得到的却是无拘无束、潇洒自由的一生。
不,或许陶渊明并没有计较过自己的得失,这种孰轻孰重的算计,和他始终是绝缘的,他只是循着心灵的方向,坦坦然然地一路走着罢了。
所以,抵达桃花源最正确的方式,大概就是让自己的心灵变得轻盈、旷达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哪怕一间小小的斗室,都容得下江湖之远、天地之大。《桃花源记》真正要说的,并非是有一处名为桃花源的地方多么安详美好,而是无论哪一方水土,只要人们是淳朴的、快乐的,那里就是桃花源。若是天下人个个敦厚淳朴,普天之下便处处都是桃花源。这,便是我这次来到酉阳所获得的感悟。我站在篱笆外凝神看着那祖孙三人分享午饭的欢愉场景,心想,谁能说这里不是真正的桃花源呢?
资料来源:中国民族报